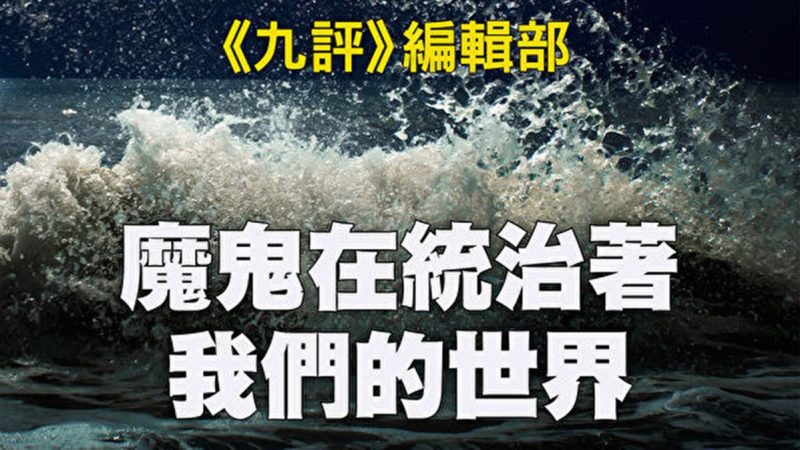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引言
自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現代女權、性解放、同性戀權利等各類反傳統運動在西方甚囂塵上,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傳統家庭。美國1969年加州離婚法開啟單方離婚綠燈,各州競相效仿,離婚—結婚比率自60年代至80年代增長超過一倍;50年代大約11%的誕生於婚姻家庭的孩子目睹自己的父母離婚,到了70年代這個比率躥升至50%。[1]根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數據,2016年美國新生嬰兒中超過40%屬於非婚生孩子。而六十年前的1956年,這個數字不到5%。在東西方傳統社會裡,貞潔的兩性關係被視為美德,如今變成被嘲弄的可笑觀念。伴隨女權運動而來的「同性婚姻權利」運動更尋求法律上重新定義家庭和婚姻。更有甚者,現任美國聯邦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委員的一名法學教授曾在2006年發起簽署一項宣言,名為「超越同性婚姻:看待我們家庭關係的戰略新視角」,鼓吹人們按自己的任何慾望組成任何形式的新家庭(包括多夫/妻「婚姻」家庭,兩對同性戀組成一個家庭等等),並宣稱傳統婚姻家庭不應該比其它任何形式的「家庭」享有更多法權。[2]在公立學校裡,幾千年來被傳統社會視為可恥的婚前性行為、同性戀不但被灌輸為正常的,甚至有的學校乾脆把任何形式的以傳統理念教育孩子視為大逆不道,以便孩子性傾向能夠「自由」發展(即毫無阻礙地發展成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者跨性人等)。如2012年羅德島學區宣布禁止公立學校舉行父-女、母-子舞會,宣稱「公立學校無權給孩子灌輸諸如女孩喜歡跳舞、男孩喜歡棒球之類的觀念」。[3]
傳統家庭被逐步摧毀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共產主義所宣揚的「消滅家庭」將先於「消滅階級」成為現實。
在西方社會裡,摧毀家庭的因素有許多方面,不但有女權、性解放、同性戀運動的變異觀念衝擊,還伴有左派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等打著「自由」、「公平」、「權利」、「解放」的旗幟變異法律制度、經濟政策,以各種顯性、隱性的形式推波助瀾,誘導人們拋棄和變異傳統的婚姻家庭觀念。而所有這一切所謂現代思潮、運動,從19世紀初發端,就帶著共產主義因素的深深烙印。共產邪靈善於不斷變化和欺騙,這使人們一次又一次被其表面動聽的口號迷惑,最終卻在其挖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傳統家庭被摧毀、人心被變異的局面,實際上是共產邪靈近兩百年來精心策劃、逐步實施的結果。
這個局面造成的直接後果是,家庭作為社會穩定的基本單元被破壞,由神的教誨而確立的傳統道德被摧毀,通過家庭承傳、培養薰陶下一代傳統信仰、價值理念的功能喪失,使年輕一代人沒有傳統理念約束,由共產邪靈直接來掌控其靈魂。
1. 神給人留下的傳統家庭
在東西方的傳統文化中,婚姻乃是由神設立,為「天作之合」,不可毀棄;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眾生,但同時神也讓男女生理上有所差別,並為男女雙方規定了各自的角色。在西方傳統中,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男人要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愛護妻子,甚至不惜「捨己」維護妻子;而女人則應當配合與幫助丈夫,使「二人成為一體」。男人負責在外「汗流滿面才得餬口」,以支持家庭,女人「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都源於人的不同原罪。類似的,在東方傳統文化中,男人為陽像天,當自強不息,有承載風雨、呵護家庭的責任;女人為陰像地,以厚德載物,當柔順體貼,有相夫教子的義務。男女各居其位,才能陰陽和合,子女才會健康成長。
傳統的家庭發揮著承傳信仰、道德、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家庭是信仰的搖籃、價值承傳的紐帶。孩子的人生第一個老師就是父母。孩子如果從父母的言傳身教中學到無私、謙卑、感恩、堅韌等等傳統美德,必將會使其受益終生。
傳統的婚姻生活也促進男人和女人自身品行健康成長,它要求丈夫和妻子以一個全新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情感和慾望,體貼包容對方。這一點和變異的同居生活有本質上的區別。人的情感總有陰晴變化,兩人高興了在一起,不高興了就分手,這種關係和一般的朋友關係沒有區別,並不需要婚姻來約束。馬克思則鼓吹情感上「無任何約束的性愛」[4],當然就是要解體傳統婚姻,消滅家庭。
2. 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目標
共產主義認為家庭是私有制存在的形式。消滅私有制,必然要消滅家庭。原教旨共產主義把經濟因素作為主導家庭關係的關鍵,當代的馬克思-弗洛伊德主義再把人的性慾視為理解家庭問題的鑰匙,二者相同之處都是把人的基本倫理道德拋在了一邊,崇尚物質、慾望,實際是把人變為獸,從而通過變異人的理念來摧毀家庭。
共產主義有一個很迷惑人的學說,就是要「解放全人類」,這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解放,也包括「解放」人類自身。解放的對立面是壓迫。那麼在人類自身的「解放」中壓迫來自哪裡呢?共產主義給出的回答是,壓迫來自自己的觀念,這個觀念是由社會傳統道德強加的:傳統的「父權」家庭觀念壓迫女性;傳統的性道德壓迫人性。共產主義「解放自己」的理論被後世的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運動繼承發展,導致反對傳統婚姻家庭、性解放和同性戀等等反傳統的觀念大行其道,成為魔鬼消滅家庭的重要工具。共產主義要推翻一切傳統的道德觀念,這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有明確的表述。
3.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
共產邪靈處心積慮破壞傳統家庭。早在19世紀初,魔鬼選擇了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播撒其思想種子。共產主義思想開拓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於1824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建立了「新和諧」(New Harmony)烏托邦公社(兩年後以失敗告終)。公社成立之日,他宣稱公社把人類從「三位一體的巨大惡魔」中解救出來,對「巨大的惡魔」一詞他解釋說,「我是指私有財產,以及以私產為基礎、荒謬的宗教和婚姻。」[5]
歐文死後,另一位有影響力的烏托邦共產主義者是法國人查爾斯‧傅立葉(Charles Fourier)。他的思想深深影響了後來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他死後,其門徒將其思想帶入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隨後又擴散到美國。傅立葉首次編造了「女權」(法文「féminisme」)一詞。在他的理想共產社會(稱作「法朗吉」 Phalanx)中,傳統家庭被嗤之以鼻,群交狂歡派對被高度讚頌為充分解放了人類的內在激情(passion),並宣稱公平社會應該對「性弱勢者」(如年老、長相醜陋者)給予照顧,以保障人人享有性滿足的「權利」。他認為,任何形式的性滿足,包括性虐狂,甚至家庭成員亂倫乃至獸交,只要不是強迫的,都應該允許。因此他堪稱當代同性戀運動(LGBTQ)新興分支「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的先驅。受歐文,特別是傅立葉影響,19世紀在美國先後出現數十個共產主義烏托邦公社,但大都曇花一現,以失敗告終。其中最持久的是以傅立葉理論為基礎建立的昂內達(Oneida)公社,維持了32年。該公社鄙視傳統一夫一妻婚姻,鼓吹群婚濫交。社員通過每週重新分配而「公平」得到和其任何心儀之人「性愛」的機會。最終創辦者約翰‧漢普瑞‧諾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因懼怕教會的法律訴訟而祕密逃亡,公社被迫放棄公妻制。諾伊斯後來著書立說成為「聖經共產主義」(Bible Communism)的鼻祖。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是其理論發展的必然。從一開始共產主義魔鬼就誘惑人背棄神的教誨,否認神,否認原罪。依照這種邏輯,本來是人類道德墮落造成的社會問題,其罪惡根源被歸結為私有制。共產主義讓人相信,消滅了私有財產,人就不會為此紛爭,但即使財產公有之後,人還可能為配偶而產生紛爭,因此空想社會主義者公然以「公妻制」為解決方案。
這些共產主義播種者創辦的共產「樂園」,或者直接挑戰傳統家庭,或者鼓吹「公妻制」,以至於各社區、教會、政府都認為這對社會道德倫理構成了挑戰,從而一致採取行動壓制。共產主義「共產共妻」的狼藉聲名不脛而走。
失敗的烏托邦公社給了馬克思、恩格斯一個教訓:公開鼓吹淫亂的公妻制的時機還不成熟。雖然《共產黨宣言》中「消滅家庭」的目標並沒有改變,他們採用了隱晦的方式陳述其毀滅家庭的理論。
馬克思死後,恩格斯完成了馬克思關於家庭的論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進一步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婚姻觀。書中指出,「歷史上一夫一妻制的出現,並不是個人性愛的結果,而是為了保存和繼承私有財產產生的。這是一夫一妻制產生的最主要目的。」恩格斯稱這種「一夫一妻制」是基於財產的「古典」模式。他認為財產公有化之後一種「嶄新」的純粹基於愛情的「婚姻」模式將會出現。沒有財產的束縛,基於純愛慕之心的婚姻,聽起來多麼的高尚!
但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解在共產主義的實踐者那裡顯得蒼白無力。感情是靠不住的。今天愛這個,明天愛那個,這不就等於是在鼓勵性亂嗎?前蘇聯和中共政權建立之後的亂性(見下一節),正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結果。
夫妻之間的情感不會永遠一帆風順,而傳統婚姻的誓言「至死不再分離」既是對神的誓約,其本身也表明了雙方在婚姻之始就準備著未來的情感可能會遇到困境,以及雙方共同應對這種困境的決心。維繫婚姻的不僅僅是情感,更是責任,對另一方、對孩子、家庭的體貼照顧,把夫妻雙方變成了有道德責任感的成熟男人和女人。
馬恩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鼓吹,在共產社會中,財產公有,家務勞動職業化,生了孩子也不用擔心,因為照看和教育孩子由國家負責,「這樣,完全不必擔憂任何『後果』──而這一切正是今天最主要的經濟和道德壓力,妨礙了姑娘把自己徹底獻給所愛的男子。這難道不足以帶來無任何約束的性交,以及隨之而來社會更寬容對待女人貞潔的榮耀和失貞的恥辱嗎?」
馬恩所鼓吹的,儘管常常用「自由」、「解放」、「愛」等詞彙掩蓋其真實含義,實際是放棄人的道德責任,使人的行為完全受慾望主宰。但無論是傅立葉還是馬克思時代,多數民眾還沒有徹底背離神的教誨,對於共產主義的淫亂思想尚有相當的戒備,即便馬克思本人也想像不到20世紀以後的人類是如何以各種藉口接受其淫亂思想和實施其消滅家庭的目標的。
紅魔安排人撒下了淫亂變異的種子,也系統安排了引誘人類屈從慾望而背離神的教誨,逐步墮落,最終讓其實現「消滅家庭」、變異人心之目標,使人落入紅魔掌控。
4. 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如前所述,淫亂是共產主義的內在基因。共產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姦污女僕,並產下孩子讓恩格斯撫養;恩格斯與兩姐妹同居;蘇聯共產黨黨魁列寧與伊內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還與一名法國女人有染,他還嫖妓並染上梅毒。另一個黨魁斯大林同樣是淫亂無比,霸占他人妻子。
蘇共奪權成功之後,馬上開始了大規模的共產共妻實踐,當時的蘇聯堪稱西方「性解放」的先導。1990年第10期俄國《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進行全面揭露,稱在性革命中的典型表現,是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柯倫泰等人,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早在1904年,列寧寫道:「淫蕩,能使精神的能量獲得釋放,不是為了虛偽的家庭價值,而是為了社會主義取得勝利,要扔出這個血塊。」[6]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三次黨代會議上,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布爾什維克一旦奪權勝利後,就要制定新的兩性關係原則。共產主義理論要求摧毀家庭,過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時期,並提出教育孩子的責任要全部交給國家。
1911年,托洛茨基給列寧寫信稱:「毫無疑問,性壓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壓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資產階級結構的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寧回覆說:「不僅僅是家庭。所有關於兩性關係的禁忌都必須廢除……我們可以向女權學習,甚至有關同性戀的禁令都必須廢除。」[7]
布爾什維克奪權後,於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寧條令》中,包括「廢除婚姻」、「取消懲罰同性戀」等內容。[8]
當時蘇聯有一個非常狂熱的口號:「打倒廉恥!」布爾什維克為了儘快地打造出社會主義的「新人類」,就通過街頭裸體漫遊來變異人的思想。他們四處遊蕩,狂熱地、歇斯底里地大喊:「打倒廉恥!」「廉恥,是蘇維埃人民過去的資產階級。」[9]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為慶祝「廢除婚姻」法令紀念日,女同性戀團體舉行慶祝活動。托洛茨基在他的回憶錄中證實了此事。他說,女同性戀遊行慶祝的消息令列寧非常高興。列寧還鼓勵更多人裸體走出來:「繼續努力吧,同志們!」[10]
1923年,蘇聯小說《三代人的愛》使「杯水主義」一詞不脛而走。小說作者是社會福利人民委員(即部長)阿歷克山德拉‧柯倫泰(A.коллонтай)。柯倫泰是一個從傳統家庭中殺到布爾什維克陣營裡尋找「婦女解放」的鬥士。小說宣揚的「杯水主義」,實質上就是性放縱的代名詞: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滿足性慾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樣簡單和平常。「杯水主義」在工人,特別是青年學生中間得到傳播。
當時的蘇聯非婚性愛大量出現,青年的性放縱已然公開。「目前我們年輕人的道德觀念應該是這樣的」,知名共產主義者斯米多維奇在1925年3月21日的《共青團真理報》上撰文寫道:「每一個共青團員,包括未成年的,以及工農速成學校的每一個學生都有權滿足性慾。這一觀念應該成為我們的信條。節制慾望是資產階級的觀念。如果某位男人看中了一個年輕女共青團員、女工人或者工農速成學校的女生,她應當儘量滿足選中她的男人,否則,她就是資產階級的『市儈』,配不上共產主義者的稱號。」[11]
不僅如此,社會上還出現了大規模的離婚運動。保羅‧坎格爾在《破壞家庭:從共產黨到進步主義,左派怎樣破壞我們的家庭和婚姻》一書中寫道:「離婚率如火箭一般躥升,在人類歷史上罕見。短時間內,似乎莫斯科的每個人都在離婚。」1926年,美國有影響力的《大西洋月刊》發表題為「蘇聯人為消滅婚姻奮鬥」的文章,報導當時蘇聯令人震驚的情況。[12]
前蘇聯性解放期間還出現「瑞典家庭」現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願者組成「家庭」。雖叫「瑞典家庭」,但是和瑞典人沒有任何關係,純粹的俄式。這一現象大開亂交和性亂之門,造成倫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戀、性病、強姦等事件激增。[13]
隨著社會主義公社的發展,「瑞典家庭」也在全蘇遍地開花。這一現象稱為婦女「國有化」或「社會主義化」。以1918年3月葉卡捷琳堡的「社會主義女性」為例。布爾什維克奪取這座城市後,就在《蘇維埃消息報》上頒布一項法令。該法令規定,16歲至25歲的年輕女子都必須「社會化」,由內務部委員布朗斯坦(Бронштейн)倡議推行,並下達命令。於是指揮官卡拉謝夫執行任務,當即就「社會化」了10名年輕女子。[14]
不過,布爾什維克很快在上世紀20年代末收緊了性政策,列寧在與婦女活動家蔡特金的談話中痛斥「杯水主義」,給它扣上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的帽子。原因是性解放帶來大批副產品──新生兒,他們無人看管撫養,家庭解體最終會導致社會瓦解。
2)延安的性開放
中共誕生之初,情況與蘇聯類似。當然,這都是同一棵毒樹上結出的不同毒果而已。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就以私生活放蕩著稱,鄭超麟、陳碧蘭的回憶錄中,瞿秋白、蔡和森、張太雷、向警予、彭述之等人情史迷亂,性態度堪比前蘇聯杯水主義盛行時期。
不只是上層知識分子型領袖,早期開闢的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建政之初,普通人生活也充分體現「性自由」。由於提倡婦女平等、結婚離婚絕對自由,出現了大量「因滿足性慾而妨害革命工作」的情況。蘇區青年還往往以「拜乾娘」接近群眾為名談戀愛,年輕女性擁有六七名性伴侶的不在少數。據《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紅安、黃麻、黃陂、光山等地方黨內負責人「約有四分之三的多數,總與數十、數百女人發生性的關係」。[15]
1931年春末,張國燾主政鄂豫皖蘇區後,即發現梅毒流行甚廣,不得不報告中央索求「診梅毒疥瘡的醫生」。多年後,其回憶錄中對當時蘇區「調戲婦女的事」、「對婦女亂來」和某些高級將領的「姘頭」仍記憶猶新。
1937年李克農擔任中共八路軍駐京辦主任,負責領取軍餉、醫藥、物資等。一次,國民政府主管部門審核八路軍的醫藥清單時,發現其中治療花柳病的藥品數量相當大。經辦人員就問李克農:「難道貴軍中得這種病的人很多嗎?」李克農一時語塞,只好編謊搪塞說是給當地百姓治病。[16]
中共20世紀30年代的性自由同樣危及了政權,不但有和蘇俄相同的社會瓦解問題,還使已婚的紅軍戰士軍心動搖,擔心參軍後妻子出軌、改嫁,影響部隊戰鬥力。而且,這種高度的性自由也坐實了其「共產共妻」的惡名。為此,蘇區才不得不頒布了保護軍婚、限制離婚次數等政策。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邪靈的各種變異思潮自19世紀開始,在西方經過上百年蛻變、演進之後,終於在20世紀60年代首先在美國大規模登場。
20世紀60年代,在新馬克思主義和各種激進意識形態的影響和鼓勵下,邪靈操縱的各種社會文化運動在美國先後登場,如嬉皮士反正統文化運動、新左派激進運動、女權運動以及性革命思潮等。這些思潮、運動如洶湧的潮水,激烈地衝擊、腐蝕美國的政治體制、傳統價值體系和社會肌體,並隨即波及歐洲。西方的社會觀念、家庭觀念、性觀念與文化價值理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異。與此同時,同性戀「權利」運動也不斷高漲。這些都導致西方傳統家庭價值觀念不斷削弱和傳統家庭模式日漸式微。同時,社會的動蕩也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如色情文化氾濫、吸毒現象蔓延、性道德崩潰、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社會福利群體擴大等。
1)鼓吹性解放
20世紀60年代發端於美國的性解放(性革命)及其隨後在全世界的迅速擴散,對人類傳統道德觀念,尤其是傳統家庭觀念、性道德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為了讓性解放在西方社會肆虐,邪靈經過了充分準備,尤其通過「性愛自由」運動(Free love,也稱性激進主義)為其鋪墊,逐步侵蝕瓦解傳統理念。從19世紀興起的「性愛自由」鄙視傳統家庭道德觀念,主張任何形式的性活動都應當不受干預,個人的性活動,包括婚姻、墮胎、淫亂行為不應受政府、法律制約。
傅立葉的追隨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諾伊斯首次提出「性愛自由」概念。
「性愛自由」在近代的主要推手幾乎都是社會主義者或深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者,如:英國「性愛自由」先鋒是社會主義哲學家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他也是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早期倡導人;該運動最知名的倡導者、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公開的社會主義者,也曾是費邊社成員,他聲稱道德不應限制人類本能的快樂,鼓吹婚前和婚外性行為;法國「性愛自由」最主要的先行者阿爾曼(Émile Armand)早期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後來發展了傅立葉的烏托邦共產主義,開創了法國個人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鼓吹濫交、同性戀、雙性戀;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者弗來明(Chummy Fleming)是澳大利亞的「性愛自由」開拓者等等。
「性愛自由」運動在美國結出的一個重要果實,是1953年起家的色情雜誌《花花公子》。雜誌採用銅版紙,給人一種「藝術」的錯覺,再加上造價不菲的彩色印刷,傳統觀念中被視為下三濫的粗俗色情題材一下子躍入主流社會,成了「高檔」休閒雜誌。半個多世紀以來它把「性自由」的毒素擴散給全球普通民眾,肆意侵襲著傳統性道德觀念。
到20世紀中葉,隨著嬉皮士文化的流行和「性愛自由」觀念被普遍接受,性革命(也稱性解放)正式登場。「性革命」是共產主義精神分析鼻祖、德國共產黨員賴希(Wilhelm Reich)首次提出的。他將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結合起來,認為前者將人從「經濟壓迫」下解放,而後者將人從「性壓抑」下解放。另一位「性解放」理論的奠基人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他的口號「要做愛,不要戰爭」,在60年代的西方反文化運動中使性解放觀念深入人心。此後,隨著動物學家金賽(Alfred Kinsey)發表《人類男性性行為報告》和《人類女性性行為報告》以及口服避孕藥的普遍使用,性解放觀念在60年代紅遍西方。值得一提的是,現代學者發現金賽在所謂的人類性行為報告中,採用了誇大、過分簡化等等手法扭曲統計數據,使很多人誤以為婚外性行為、同性性行為等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對性解放、同性戀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7]
一時間「性解放」成為現代社會的時髦道德價值觀。在青少年圈子裡,放縱的性生活被視為正常,十幾歲的女孩若敢於承認自己是處女,會受到同伴的恥笑。資料表明,1954年至1963年之間達到15歲的美國人(也即60年代的青年)中,82%的人在30歲之前有過婚前性經驗。[18]到2010年代,結婚前仍為處女的新娘僅為5%;18%的新娘婚前有過10個以上的性伴侶。[19]「性」成為大眾文化的流行主題,以性描寫招徠讀者的「文學作品」充斥市場,「兒童不宜」的X級影片受寵於各大影院。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1)女權運動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
女權運動是共產邪靈利用來破壞家庭的另一駕輕就熟的工具。早期女權運動(也稱第一波女權運動)18世紀發端於歐洲,主張婦女應當在教育、就業和政治方面享有與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紀中葉,女權運動的中心從歐洲轉向美國。
第一波女權運動發生時,傳統家庭觀念的社會基礎依舊強盛,這時的女權運動並不主張直接挑戰傳統家庭。當時影響力顯著的女權主義者,如18世紀英國的瑪莉‧烏絲東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9世紀美國的瑪格麗特‧芙樂(Margaret Fuller)、19世紀英國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都主張一般女性婚後應以家庭為主,女性的潛能主要是在家庭領域裡發展,女人充實自己是為了家庭(如教育子女、管理家政等);而那些特別優秀的特殊女性,應該不受任何阻礙,自由發揮她們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較長短。
20世紀20年代後,隨著婦女選舉權獲得各國法律承認,第一波女權運動漸趨平靜。此後隨著大蕭條的衝擊和二戰的影響,女權運動基本偃旗息鼓。
與此同時,共產邪靈也早早埋下了摧毀傳統婚姻家庭和性道德觀念的種子。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在19世紀就為現代激進女權運動奠定了方向。被稱作女權主義之父的傅立葉宣稱婚姻把婦女變成了私有財產,歐文把婚姻詛咒為「邪惡」,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被一批女權主義者繼承並發展,如19世紀女權主義者萊特(Frances Wright)繼承了傅立葉的思想,主張實現女性的性觀念自由。英國女權活動家惠勒(Anna Wheeler)繼承了歐文的思想,激烈譴責婚姻把女人變成了奴隸等等。同時,社會主義女權活動者也是19世紀女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法國最有影響的女權刊物,如法國第一份女權主義日報《婦女之聲》(La Voix des femmes)、《自由婦女》(La Femme libre ,後更名為《婦女論壇》)、《婦女政治》(La Politique des femmes)、《婦女評論》(La Politique des femmes)等,其創辦者或是聖西門烏托邦主義者(Saint-Simonian),或是傅立葉的追隨者。由於當時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緊密聯繫,遭到當局嚴厲審查。
我們看到,當第一波女權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的同時,紅魔也同時安排了各種激進思潮衝擊傳統家庭、婚姻觀念,為隨後到來的更加激進的女權運動作了鋪墊。
第二波女權運動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隨後波及到西歐及北歐,並迅速擴展到整個西方世界。60年代末期的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動蕩不定的時期,伴隨著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各種激進的社會思潮紛紛抬頭。女權主義趁機以更激進變異的面目出現並風行世界。
奠定這一波女權運動第一塊基石的是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奧祕》,以及該書作者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發起成立的全國婦女組織(NOW,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該書作者從一個郊區中產階級家庭婦女的角度,激烈批評女性的傳統家庭角色,認為傳統的快樂、滿足、幸福的家庭主婦形象是所謂「父權社會」塑造的迷思。她認為中產階級的郊區家庭是「美國婦女舒適的集中營」,受過教育的現代婦女應該跳出滿足於相夫教子的成就感,在家庭之外實現真正的自我價值。[20]
數年後更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主宰了全國婦女組織,繼承並發展了弗里丹的女權思想。她們認為女性自古以來都是被父權文化所壓迫的。她們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並主張徹底變革社會制度,徹底變革傳統文化,在經濟、教育、文化、家庭諸方面進行全方位的「鬥爭」,實現女性的「平等」。
把社會按照某種方式劃分為受壓迫者和壓迫者,從而鼓吹「鬥爭」和「解放」、「平等」,這正是共產主義的核心要旨。傳統馬克思主義以經濟地位劃分人群,新女權主義則以性別劃分人群。
事實上《女性的奧祕》的作者貝蒂‧弗里丹並非如書中所暗示,是一個厭倦家庭瑣事的中產階級郊區家庭婦女。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的教授霍熱維茨(Daniel Horowitz)於1999年寫了傳記《貝蒂‧弗里丹及其〈女性的奧祕〉的出籠》。他的調查揭示弗里丹從大學時期到上世紀50年代,一直是激進的社會主義活動家,曾先後擔任幾家由共產黨主導的工會組織喉舌報刊的專業記者,霍熱維茨並找到她當年寫的這些文章。她在伯克利加州大學期間加入共青團,並兩次申請加入美國共產黨,但美國共產黨沒有接受(因其黨外身分更能發揮作用)。她自己授權的傳記作者朱蒂‧函妮斯也不諱言她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21]
美國學者凱特‧薇根特(Kate Weigand)在《紅色女權主義》一書中指出,實際上女權主義在20世紀初到60年代的美國並沒有沉寂。包括安東妮(Susan Anthony)、弗來克斯娜(Eleanor Flexner)、勒娜(Gerda Lerner)、米拉姆(Eve Merriam)等等一大批有共產主義背景的紅色女權主義作者,在這一時期為隨後到來的第二波女權運動進行了多方面的理論鋪墊。安東妮早在1946年就運用馬克思的分析方法,以白人壓迫黑人作類比,指出男性同樣壓迫著女性。只是由於受麥卡錫反共影響,共產主義臭名昭著,她們從此閉口不談自己的紅色背景。[22]
在歐洲,法國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代表作《第二性》引領第二波女權風潮。波伏娃早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1941年她與共產主義者、哲學家保羅‧薩特及其他作家一起創建了法國地下社會主義組織「社會主義與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隨著60年代其女權主義聲名鵲起,她宣稱不再相信社會主義,只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
她主張「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鼓吹雖然性(sex)是由人的生理特徵決定的,而性別(gender)則是在人的社會性的影響下後天所形成的一個自我認知的心理概念;認為女孩順從、乖巧、愛撒嬌、富於母性的「女性氣質」全都來自後天的「父權社會」精心設計的「神話」,為的是維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她主張女性衝破傳統理念,實現不受約束的自我。這種思想實際為同性戀、雙性戀、變性等等各類變異觀念提供了溫床。此後各類形形色色的女權思想層出不窮,基本都繼承了女性不平等來自於傳統「父權社會」的壓迫。因此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傳統家庭婚姻觀念是實現女性平等的主要障礙。[23]
波伏娃認為婚姻讓女人受制於丈夫,「同妓女一樣令人噁心」。她同薩特保持終身情人關係而拒絕結婚,與此同時她也和其他男人保持「偶然的愛情」,同樣的,薩特也擁有幾位其他女人的「偶然的愛情」。她的婚姻觀是當代激進女權主義者的主流態度。事實上,這種複雜混亂的性關係正是烏托邦共產主義先行者傅立葉19世紀所設想的公妻制。(未完待續)#
(點閱大紀元《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大紀元)